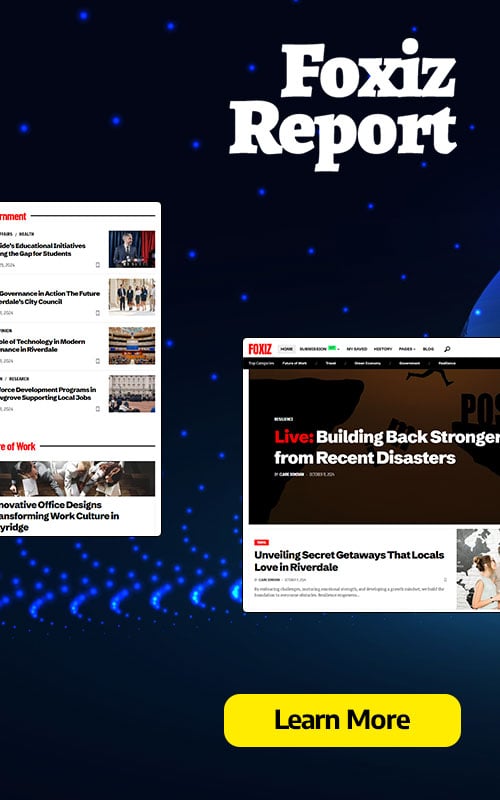Editor
聖經考古學有助認識舊約記載的歷史
雖然現在存在著這些個别的問題(同樣考古學資料會有不同的解釋);但仍然毫無疑問可以相信一點,就是通常發掘出來的文物都有助於確定舊約記載的歷史之真實性;而不是好像上一代的自由派學者一般,欲以此貶低聖經的價值。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在1868年於底本(Dhiban)被發掘出來,這提供了摩押方面的資料,證實了以色列國的王暗利(公元前885-874年),控制了北摩押地,也在任期內收受了豐厚的進貢。 此外,魏士曼(D.J. Wiseman)在1956年首次發表出來的巴比倫年表(Babylonian Chronicle),不單證實了舊約中耶路撒冷於主前597年淪亡的記載,更就著主前601年埃及與巴比倫這場不為人知的戰爭,揭示其戰爭實況:在這場戰爭中,雙方的人力設備都損失慘重。這些例子說明了考古學的研究能提供更多有關古代歷史的資料,而且藉著考古學的發現去幫助研究舊約純歷史方面的記載,甚至是希伯來的社會、政治、宗教、生活方面,這做法也是正當的。 關鍵詞: 巴比倫年表 / 底本 / 魏士曼 / 摩押石碑
聖經出土文物的尋獲與價值
在亞瑪拿發現的信件,首次供給學者國際外交往來書信的樣本,這些信件是用楔形文字寫成的;也同時指出在主前二千年左右亞甲文(Akkadian)已被承認為外交文字。同期的赫人(Hittite)條款也在波亞茲科(Boghazkoy)發現,顯示出當時典型的封建宗主國與租地國之間的平等條款之結構;這發現對今日了解申命記之文體及神學上之特色是十分重要的。在馬里及努斯發現的楔形文字石版,提供了許多有關希伯來族長時期生活狀況的資料:在亞拉拉克(Alalakh)的發現也補充不少這方面的資料,而且被認為其記載較馬里及努斯的在年期及地理上更接近族長時期。 當考古學家發現到古代的宮殿文物儲藏庫或廟宇時(諸如在馬里發掘到的),他們即感到很幸運;若他們在開始一件考古工程的時候,發現到這些,這感覺定必更强烈了。同樣幸運的事,就是發現到有儲藏古董嗜好的古代君王建築的圖書館,就如在1853年,拉森(Rassam)在尼尼微皇宮古址發掘時,發現一座由亞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建造的圖書館。 這具價值的巨大收藏,包括有十萬石板,它們是由亞述國最後一個有文化而又博學的君王在任內累積而成的。由發掘出來的文物顯示,亞述巴尼拔曾下令文士去收集及抄寫廣泛不同性質的資料,包括有歷史、文法、法律、文學、醫藥及天文學。除此之外,亞述巴尼拔更收集了不少詩篇、信件、詩歌、符咒、字典、不同類型的商業合同,及一百多塊石塊記載著一特别而稀有的題目。 繼這些發現之後,其他幾項重要的楔形文字儲藏庫也在不同地點發掘出來,大大增加了研究古代近東的資料來源。自從1849年在尼尼微發掘出亞述巴尼拔的圖書館及有關古物後;1887年發現亞瑪拿的石版;1889年開始在尼普爾(Nippur)發掘楔形文字記載的古物,至今仍然有考古學家繼續發掘;1906年在波亞茲科發現赫人的文物儲藏庫;1925年在努斯發現一批石版;在烏加列(Ugarit)的重要文字記載則在1929年被發現;自1936年,馬里的巨大文物儲藏庫就開始被發掘;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奇妙地在1947年被發現。除了以上的重大發現,更有許多有輔助作用的古物;例如刻有楔形文字的圓柱、六角柱,一些刻有文字的泥磚、石塊、不同的信札、貝殼、石碑、蒲草紙文件、刻像,以至一些日常用品。 關鍵詞:聖經考古 / 亞瑪拿 / 亞甲文 / 馬里 / 烏加列 / 楔形文字 / 波亞茲科 /…
聖經考古學的資料來源
古代近東古蹟,雖然是文字上的記載,但明顯地亦屬考古學的範圍之內。這些資料其中的部分遠在考古學成為一門科學之前已找到,然而大部分資料都是近代在近東散佈各處不同地點發掘出來,學者遂能掌握到這類資料。這些文物有些是屬於圖畫性質的,例如在巴比倫及亞述國之皇宮及廟宇中的浮雕,又如埃及的皇宮、廟宇、金字塔及墓室內部精心繪製而成的美麗圖畫。 但在古代文化的頹垣敗瓦中,人們幾經艱苦才能發掘出文物。也有許多不是屬於圖畫性質的。在這方面而言,考古學家的技巧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因為他不單經常要小心準確地發掘破碎的古物,更要負責將它們重新組合,否則他們就無從考究發掘出來的物品。不錯,今天的考古學家有各種不同壯觀的電子及放射性碳元素的機器幫助工作,但仍要倚賴考古學家耐心移除古址上的泥土,準確地重組古物,正確認出寫在古物上的文字,而這些文字是經過風雨長期沖洗,並且是當代人在不經意的情況下,寫下的不易明白的文字;考古學家又要按著出土的陶器及別的有關資料去製造正確的年表;並且須將某個古址上找到的資料與另外其他古址中已得的資料比較及尋求其間的關係。 很明顯地,這些活動都可以超越了考古學家的基本工作;本來他主要的任務就是去發掘人類過往歷史的遺物,但對研究近東的學者來說,他有責任評估被發掘出來文物的價值,估計這些文物對近東人整體生活的重要性。因為當時的國家經常彼此接觸,任何考古學上的發現,都常對整個近東的研究有比初步估計更大的關係。 關鍵詞: 聖經考古 / 聖經考古學 / 古物上的文字
舊約時代的家譜
家譜對於米所波大米人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在馬里(Mari)及努斯(Nuzi)發現的。 雖然至少自主前二千年始,人類已採用民事反宗教的曆法,通常日子的計算可以這些曆法為根據,但最常用的計算個人歷史之方法卻是以個人家譜或家系圖為本。這些名單沒提及帝王的任期,也不理會其他日子或年份,有的只是寫在末頁或在碑上記下日子,它們注重的只是顯要人物及他們的家庭子孫等。 對於許多人來說,他們接觸過的歷史,就只有這種描寫代代子孫的族譜,這現象在舊約中亦是明顯,事實上族譜就是一種歷史的著作。撇開個人的問題,無論如何,在馬里和努斯發現的族譜提供了許多有關當時社會的風俗習慣的重要資料(例如認養的法則),以後的內容會更詳細討論。 關鍵詞:家譜 / 家系圖 / 米所波大米 / 馬里 / 努斯
舊約時代的古代來往書信
外交的來往書信亦是研究古代近東的重要資料來源,不論罕模拉比時期的文件抑或是較為人熟悉的主前十四世紀亞瑪拿(Amarna)書信,都屬於這類文件。 各類的商業文件也從米所波大米的各古址中發掘出來,這使我們在意想不到之際,知道主前三千至二千年的社會發展原是那麼進步的。好像名單等這些資料的發現,對於重整當時各時代不同的地理區域之關係有極大價值,並且至少顯出當時近東居民遷徙的動向。 關鍵詞: 古代來往書信 / 罕模拉比 / 亞瑪拿
舊約時代的旅歷記錄
遊記的文字記載亦是對研究古代近東的地理及地形學有很大幫助,因為當時的城市名單中仍然有許多到現在還不知所在的市鎮。人的名字亦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因為它使我們知道,在埃及中王國時期,巴勒斯坦及敘利亞居民通常都會接待其他民族。 這一類的文字記載,更顯示許多有關近東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辛努黑的故事》(Tale of Sinuhe)便是一例,這有趣的埃及故事描述了一個生於主前二十世紀的富翁,在年老的法老王阿蒙涅姆一世(Amenemhat I)離世時,逃往巴勒斯坦,尋求政治庇護。以差不多這樣形式,描寫埃及後期歷史的內容,亦見於《雲阿蒙遊記》(Travels of Wen-Amun)。這遊記顯示在主前一千一百年左右,埃及的勢力衰退,被鄰國輕視的情況,故事描述埃及祭司雲阿蒙欲建造諸神之王阿蒙的聖舟,前往腓尼基去購買香柏樹時,遭不少侮辱挫折的經歷。 關鍵詞:旅歷記錄 / 埃及 / 辛努黑 / 雲阿蒙
舊約時代的棺文
有關古代米所波大米之信仰的其他資料,可取自他們向衆神獻呈的詩歌、衆神的名字、他們之間的關係、主要功用,以及用來作各種崇拜指導包含儀文細節的經文。從埃及得到一些著作,其中有《死亡之書》(Book of the Dead),這書收集了不同的魔術咒語,他們認為這些咒語能幫助已死的人去面對陰間統治者歐西里斯(Osiris)。 事實上這些資料就是棺文(Coffin Texts),由中王國時期(Middle Kingdom)開始存在,這些棺文是抄寫在蒲草紙上,然後貼在死者遺體旁的棺木上。棺文就是有能力的魔術咒語,在葬禮中背誦,其被稱為「棺文」是因為被寫在棺材的邊牆上,以方便死去的人在來世可隨手拿來用。 「棺文」也其實是金字塔文(Pyramid Texts)的一種,是魔術咒語及靈符的一部分,這些碑文被刻在金字塔的牆上就是為了給在金字塔內死人的方便,因為他們深信死去的人比眾神或活人更需要咒語及靈符的幫助。從這些資料看來,很明顯地在古埃及「宗教」的行動或與他們敬拜之神的接觸,都有魔術的性質。的確,埃及的文字中像希伯來的文字一樣,都沒有一個字的意思是「宗教」,最接近其意的是用「魔術」或「魔力」。 關鍵詞: 米所波大米 / 死亡之書 / 棺文
舊約時代的宗教史詩
宗教的史詩在米所波大米是十分普遍的。這些作品提供了許多有關古代迷信的信仰及習俗的有關資料。根據早期蘇美人神話資料寫成的創世史詩,就是在巴比倫第一王朝寫成,原來的形式是寫在七塊石板上,每石板上平均有一百五十行詩。內容描寫各神的起源,涉及巴比倫的守護神瑪爾杜克(Marduk)與鹽海水之神提亞麥(Tiamat)之戰爭,並提及在天神控制的宇宙下人類的被造經過。巴比倫第一王朝另一套著名的文學作品,也是根據早期蘇美人神話寫成的吉加墨施史詩(Epic of Gilgamesh),內容描寫在主前三千紀末期的時候,以力(Uruk)的統治者吉加墨施的特别經歷。第十一塊石板十分重要,其上保留了巴比倫對洪水滅世的傳統記載,其內容細節與創世記的描寫有不少相同之處。 關鍵詞:宗教史詩 / 米所波大米 / 創世史詩 / 巴比倫 / 蘇美 / 巴比倫洪水記載
舊約時代的帝王名表、年鑑、功績
帝王名表在早期米所波大米就已編修,特別是蘇美的名表對於建立歷史年表更具價值。在這些文件中,有一部分卻因某些王任期的長短,引起不少意料不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華得 -- 白蘭度(Weld-Blundell)棱柱體,上刻有吾珥第三王朝(蘇美復興)的帝王名表,一方面這名表按年期先後提供了八個蘇美統治者的年份,但另一方面它記述每個帝王在位的年日,卻是無理地長。 在古埃及的文物資料中,有一象牙板,將最初兩王朝的帝王列出,因為其性質特別,所以能大大幫助研究者去研究早期埃及的歷史,亦為他們提供重要的資料。埃及最初五個王朝的歷史記載,則可見於以年鑑形式寫成的巴勒莫石碑(Palermo Stone)上,將這著名的石碑鑑定為公元前二千四百年的物品,應該是沒有甚麼問題的了。 以年鑑的方式記事在古代近東一帶在古代來說是非常普遍的。每個帝王任內若有任何大事記錄,若不是被刻在皇宮、墓葬廟宇、金字塔或石碑等的牆上,就是用其他相似而又合適的方法記錄給後人看,這種做法毫無疑問,能使記錄永久留下,亦使現今的學者能接觸到古代近東著名統治者的功績,例如陶特姆斯三世( Thutmose III)、蘭塞二世及三世(Ramses II,III)、示撒(Shishak)、撒縵以色三世(Shalmaneser III)、西拿基立(Sennacherib)、撒珥根二世(Sargon II)、以撒哈頓(Esarhaddon)、古列大帝(Cyrus the Great)、大利烏大帝(Darius the Great) 。 關鍵詞:帝王名表 / 蘇美 /…
舊約時代的科學記錄
巴比倫及埃及的古代醫學及科學文字,最低限度可以追溯至主前三千年。 由古代蘇美的原址發掘出來的石版,包括了與科學有關的資料,例如天文學、數學、地理、藥劑、醫學等,這顯示蘇美的文化是多麼先進的。古埃及的醫學傳統,大部分很可能是興起於主前三千紀末期,在後期稍加改良增添然後傳出,成為醫學及外科手術方法的課本及醫學個案。 在眾多的埃及蒲草紙文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在公元1862年發現。其中包括了在底比斯發現的史密夫(Edwin Smith)外科手術蒲草文件,還有埃伯斯(Ebers)蒲草文件,這些文件是涉及藥劑及醫學的。許舒得(Hearst)蒲草文件內容相似於埃伯斯蒲草文件,是在1899年上埃及地發現的。彼得利爵士又在1889年在埃及發雍(Fayyum)發現迦漢(Kahun)醫學蒲草文件。在這麼多重要文件之外,還有大柏林(Greater Berlin)蒲草文件,它的時代雖然比埃伯斯蒲草文件遲一些,但顯然是根據更可靠的資料寫成的。 現今在英國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法國巴黎的羅浮宮博物館、美國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等,都儲存許多巴比倫及埃及的古代醫學及科學之文字記錄,是研究當時背景的好資料。 關鍵詞: 巴比倫 / 埃及 / 古代醫學 / 古代科學 / 蘇美 / 大英博物館 / 羅浮宮博物館…